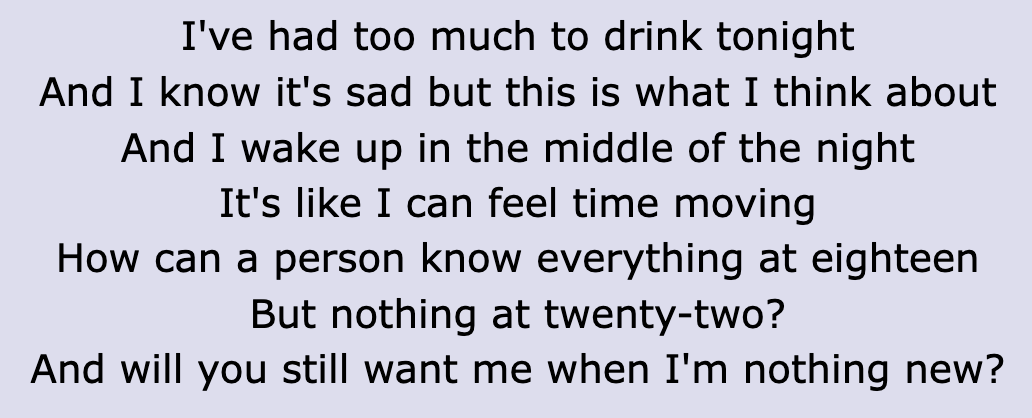泡沫
如果再问我,一个亿和北大学历我选哪个,我发现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自信的说,钱没了可以自己赚,而北大错过就是错过了。
毕业季,看着前辈们的毕业致谢,我甚至无法想象届时的我,会觉得大学四年有什么值得我去感谢,仿佛18岁后一切所谓的成长和这个硕大的招牌唯一的关系,都仅在于我于那方小小书桌前度过的无数个艰难的夜晚。至于其他的快乐,都与这个牌子无关。
或许是时间的沉淀尚未来到,但人们所说的所谓名校可以带来的知识、阅历、人脉、青春记忆、人格培养、社会地位,我却并没有感受到多少。如果说我真的有所成长,那也大概是发生于在这块摇摇欲坠的招牌所承载的幻想逐渐破灭时,我所作出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可称作是抗争的东西。沉默地对抗学业的枯燥与意义的虚无,逃避形式的枷锁与教条的束缚,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,我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厚厚的茧壳。茧壳只知道破壳,却不知道破壳之后,明天又会是怎样。
长大的过程中人们都说,女生看的世界越多,眼界越开阔,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更自信,更懂得追求精神的充实而非物质的堆砌。但我翻看着硬盘里六十多G的照片,却很难说,除了被捶打重塑的物质观,我还得到了什么。
在北美旅游的时候,为了省钱,我几乎没有住过正规的酒店,去哪里都住的五十一晚的青旅,假装听不见周围人的鼾声和高低床老旧的嘎吱声,假装看不见浴室地面的污渍和墙上的头发。从康村到DC,为了省下近一倍的飞机票钱,我坐了十个小时的大巴,手忙脚乱地在座位上吞咽走了十个街区买的一美元披萨。从纽约回香港的时候,国泰莫名其妙地给我升舱到公务舱。公务舱和经济舱只隔一道薄薄的帘子,帘子背后是婴儿的哭声、肩膀与胳膊的摩擦和无处安放的腿,帘子前是我喝完香槟之后安然入睡的9个小时。那16个小时与我来时三度转机狼狈的27个小时产生了鲜明的对比。
你问我过得是否拮据,当然不是。不管从什么维度来看,我的生活都可称舒适,甚至这些抱怨也是一种奢侈。越过这些表面的门槛,这些颠沛流离仍然是快乐而珍贵的,我的精神依旧是充盈的,思想依旧是演进的。但在追求旅行中的精神果实的路上,在显得如此漫长而割裂的去年里,在人文的天空之外,这样的对比让我第无数次感受到,人在被剥离原生环境的状态下才会懂得,什么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在开蒙的年代里,钱只是获取想要东西的手段,钱本身没有意义。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,它当然不能是生活的全部意义,但它本身就有意义。
从小到大的教育都在告诉我,梦想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。但当我看着北京水涨船高的物价,想给妈妈打电话诉苦,却听见电话里的她说,妈妈跟客户喝酒喝醉了,为了给你赚学费的时候,梦想显然是个物质得不能再物质的概念。
梦想是在地铁站旁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,是一辆丰田凯美瑞,是每天晚上都能自己做饭的小厨房,是le creuset直径20cm的蓝色圆形铸铁锅。这样的追求高不高,因为我没有比较对象,我也不知道——大概是不低的,毕竟所谓中产都是谙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的人。但令我沮丧的不是这些符号的平庸——相比十二岁壮志凌云想当外交官的我而言,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没有太高精神追求的人。不管是因为我过早悲观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,还是以现实主义为借口逃避大叙事加于我头上的责任,我坦然接受我违背现实期待的平庸。真正令我怅惘的是,从什么时候起,未来对于我来说只剩下物质的想象。
过年的时候全家一起去群光逛街,我在le creuset的店面里,把所有的锅摸了一遍又一遍,然后走过商场六层的吸尘器、刀具和床上用品店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不为买不起这些东西而哭——过早懂事的我早就明白了欲望的上限,只要在范围之内,想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我为我的庸俗而哭,我为拿走商场里最便宜的鸡蛋而哭,我为我攥在手里的存款而哭,我为我别扭的自尊心而哭,我为我自作聪明的现实主义而哭。但我什么也做不了,我只能哭。